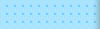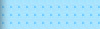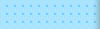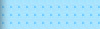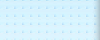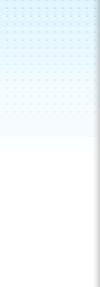“十三五”规划已经执行过半,2019年将逐步进入新一轮的“规划时间”。“十四五”起点的2021年,既是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节点,也是面向2035年“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的起点年。所以,本次五年规划呈现出与中长期规划“历史性交汇”的典型特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已经发布,据说《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2021-2035)》也在低调谋划之中,相信其他领域的“十四五”规划或至2035年的中长期规划制定都将陆续展开。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双一流”、“十四五”和综合改革这三大核心命题也必然呈现历史性交汇,主题话语的内涵指向有所不同,但无疑学科建设依然是重要内容,这是由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的地位所决定的。可以想见,在整个高等教育运行范式,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绩效评价体系及深层次的院校地位形成机制等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的前提之下,学科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规划“套路”估计不会有多大改变。所以,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高校“十四五”规划的学科规划将如何“螺蛳壳里做道场”,尽力做出新意、创意并有指导意义,就是迫切需要提前思考和谋划的事情。
思之所及,提出以下想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一、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协同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把基础研究摆在了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突出位置,具有时代性、前瞻性、战略性,继而科技部、教育部等也提出了若干重大举措。虽然基础研究不等于基础学科,但后者明显是前者的重要指向,何况基础学科还承担着科学通识教育、科学精神培育、科学文化营造等“软功能”,不可谓不重要。事实上,我们常在很多场合把二者置于同一层面上进行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愈发深入,基础研究似乎就被“忙起来顾不上了”,而与市场更加接近的、易于“变现”的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得到了更多青睐。近年来,不少高校都有“泛绿”趋势(如果应用端为绿的话),除了少数高校传统基础学科“一优独大”,其他高校都在向应用学科拓展、转移、趋同。但无论学界的认识多么清醒,无论规划制定的多么正确,都扭转不了事实上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的学科发展风向的转变,主要源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科技创新水平不断跃升,尤其是实业界就越发现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关键瓶颈;二是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构筑基础研究先发优势成为必然选择。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心态、政策、行动上的转型是大国崛起的必然、必须、必要,已在美国、德国、日本等曾经的后发国家身上得到过充分体现。
大胆猜想,各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基础学科的分量一定会加重,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如何协同,进而发挥学科生态系统的整体竞争力。这一点恰恰是院校实践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处理的问题。从近年来的高校建设经验来看,寄希望于在既有学科框架下实现学科交叉或实质性跨学科研究,无论是建构多少实体性学术平台,结果已经证明并不理想。
因此,“十四五”要走“问题导向”的学科协同道路,原因在于:一是宏观政策鼓励,可能能拿到更大的资源支持;二是超脱于原有学科/院系体系,易于学科链条搭建和跨学科活动的形成。但也需要边界条件的保障:一是学术牛人的带领,二是方向选择的对头,三是组织机制上的可持续。
二、稳定方向与前沿开拓的统一
据不少报告显示(多以发文为依据),中国大学所开展的前沿方向研究与国外一流大学迥异,孰优孰劣不好回答,这涉及到科学发展规律、国家迫切需求、学科发展基础等多个维度的“边界条件”。但是,新兴、交叉、前沿方向涌现不足,从事相关研究的人才/团队、平台、项目得不到充分支持,确是不争之事实,这也正是常言所说的“学霸学阀”的问题。
国家走向全球科技创新前台或“无人区”的进程中,同步领域弯道超车,前沿领域下先手棋,陈旧领域果断放弃,是必然选择。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无论是什么学科,在牌子、台子、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都面临着想做的事情太多与资源条件尤其是人手不足之间的矛盾,问题集成到学校整体就是如何协调好稳定学科方向和开拓前沿领域的问题。有的传统学科,有渠道、有经费来源、目前尚有市场需求,尤其是有牛人、牛牌(子)支撑,很难转型,这对学校而言是个大难题。目前,学科方向肯定不单单关涉科学研究,已经日趋影响到人才培养,不少人提出建构新的学科(如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的理由就是“科技创新需求→人才培养需求”。
方向选择是否合理,长远内可能影响一个学科甚至整个学校在某领域的影响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为此,这个问不可不察也。世界一流大学的院系内部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演变,但其学科体系“一万年不变”的,尤其是表征在院系设置上的学科体系。这就说明,无论科学研究或社会需求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作为知识分类内涵上的学科体系,(可以)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所以,“十四五”规划,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即抱残守缺全然不顾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即完全抛开优势学科方向之基础而忽左忽右。中间的灵活地带,要通过重大资源获取、领军人才引进等方式得以激活,并使其扮演融合多方、孵化前沿、活跃学科系统的功能。
三、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融合
在中国提及学科建设,人们感其内涵的第一反应可能会很多样,但绝对不会是人才培养。虽然当今对大学使命的认知有回归培养人才的趋势,但真正在实践上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的情景少之又少,这也反映在各种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中。我们注意到,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已经把人才培养放到了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十四五”规划不改善人才培养的实现环境,将真是会动摇大学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将会逐渐显现出来优势学科在社会影响力上式微现象。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国大学并不直接和完全面向社会、市场、学生及其家长这个“客户”办学,才带来了即使并不十分注重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但却依然可以“大发展”的怪事儿。但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不但政策上有立德树人的要求,而且上述“客户”需求的倒逼效应也在增强。这一点,我曾经在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构建高校与社会的深度互动关系》,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03日),不再赘述。
从科教结合到科教协同再到科教融合,对科教关系的强调似乎是在加强,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解决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高水平科研活动、成果、条件支撑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记得有次调研中,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博士生(含直博生、硕转博)名额十分有限,他不得不或者说不自觉地从带过课的本科生中去挖掘潜在科研才俊并着力拔擢,效果似乎还不错(当然也是用“发文”的质和量来衡量)。这带给我的启示是,真正的科教融合或者让学者更加注重人才培养的实现,功利化的制度设计(如使学生的发展与学者的学术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是这样,我们真是“不择手段”去实现崇高目的了。
毫无疑问,在这个话题下,相比研究生,本科生更加需要关怀。而接近问题的思路,一要在科研任务上给研究人员松绑,解放其时间和精力;二要适度功利化制度设计,使研究人员看到好处;三要把人才培养的底线要求再做严,真正实现培养是本分主业、科研是可选项的目标。当然,这是一套复杂的制度设计。
四、发展绩效与责任机制的贯通
这是个与“综合改革”话语密切联系的问题,却关涉学科的可持续、高质量、顶尖化。
大学是松散结合的联盟型组织,映射到学科建设上表现为责任机制缺失的问题,如果大家足够自觉或大多数人足够自觉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事实上,要么是大家不足够自觉,要么是没人敢冒完全放任的后果风险。学校领导者权力覆盖面宽,政治号召、愿景激励、战略规划的权威力在下传中层层衰减,实践中往往很难影响基层学术组织和教职员工(遑论学生)的行为模式。院系领导者具备较高的学科归属关系,尤其在一个院系拥有不止一个一级学科的情况下,加之任期制的影响,其责任机制状况取决于个人素养的情况较为普遍。
在不少大学的不少情况下,“学科负责人”与院系的负责人并不统一,进而造成龃龉与损耗。“院为实体”已成为普遍实践,院系逐渐成为配置重大资源的权力中心,部分大学的校→院权力下放进程还在加快。而在院系内部,哪个学科(当然是国内的教育部以及学科概念)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全靠“人品”了。
笔者以为,学科负责人很难承担学科建设绩效责任,更应该承担学术领军者角色,起到凝聚人才、学术咨询、居间联络等作用,可谓之“学术经纪人”。院系负责人应该作为学科建设绩效的首要责任人,学术责任可以借助于组织治理手段(如班子考核)和绩效考评手段(如“双一流”评估)得以准确传导。在资源配置权逐渐向院系层面下放情况下,院系负责人(或院系班子)权力放大,自然应配以更大责任,实现权责统一。
五、条件支撑与重点战略的配合
建学科与建大学一样,都是所谓非常烧钱的事儿,就如学界经常引用的洛克菲勒捐资数亿美元助力芝加哥大学短期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例子。当然这个“钱”要宽泛地理解为包括场地、设施(设备)、经费、研究生名额、平台等多方面的支撑条件。
长期以来,发展规划中虽也提及学科群、学科生态、学科体系等概念,尤其是在应对“双一流”政策和学科评估情境下,不少高校“十三五”规划做了力度各异的重点发展设计,但贯彻得并不彻底。大学是松散结合的学术组织,每个组织单元甚至不少领军人物都是一个话语中心,撤并学科常常撤而不消、撤而不倒甚至改头换面死灰复燃、重树大旗,重点发展战略被搁置、被消弭、被扭曲的情况并不少见。表现在资源配置上,就是重点设计的战略性学科投资经常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或半平均主义的操作方案。最终,学科调整政策仅在少数高校深入推动,并取得成功。
事实上,重点学科发展战略如不切实配以重点资源投入政策调整并持之以恒,则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很多时候,资源的平均分配,即使是重点发展领域投入略多,也很难形成对重点发展领域的正向激励,这或许与人的心理类似。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发展资源的多元化(如前所述),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重点发展学科不可能得到所有资源的倾斜,而是大家“各有所获”,这是资源分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浙江大学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就是为了使条件支撑与重点战略更加匹配。实施的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优势特色学科发展计划,通过各项学科建设计划的分层分类支持,进一步落实“高精尖缺”导向;去年以来又相继启动“双脑计划”等多个学科会聚计划,真正把多种资源向重点领域、特色方向上倾斜,并通过增量资源的有选择投入,来实现学科体系化布局,高峰凸显、高原崛起、综合交叉、动态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十四五”,改革将继续深化,宏观资源瓶颈可能会显现,必须再动真枪,刀刃要向内。谁反应快,谁力度大,谁就可能在学科体系化布局中占得先机。